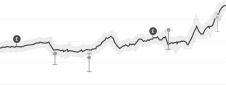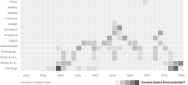Signed Baishi, Sanbaidanyinfuweng, with two artist seals
说 明 胡橐上款。胡橐(1925-1994),号橐也,河北涿县人。胡佩衡子。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年调到北京中国画院工作,任艺术室干部。1970年,随妻子穆宝琛所在北京天坛医院迁移到甘肃省天水市,任天水市雕漆厂工艺美术师。1980年调回北京画院,1994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对古代画家,齐白石用力最多的是八大。1918年,他题《菊石小鸟》说,自从在南昌见八大作品,“匆匆存其粉本,每为人作画不离此乎。十五年来所摹作真可谓不少也。”直到上世纪20年代前期,仍有不少临仿八大之作。
白石学于八大的,一是冷逸画风;二是减笔画法;三是鱼、鸭、八哥、乌鸦等的造型。其背景是:约四十岁前后,他由民间画师向文人艺术家转变,八大遂成学习的首选人物。摹习八大对促成这一转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衰年变法以后,他抛弃了八大的冷逸画风,突出了个人风格和创造性,但并没有丢弃八大的减笔大写意模式。在1945年的一则题跋中,他曾对丢弃八大画风表示“殊堪自悔”,但这种自悔只能看作成功者回首往事时的一种情感歉疚,而不是对变法革新的否定。1951年,他题早年所画的《秋梨与细腰蜂》云:“此白石四十岁后作。白石与雪个同肝胆,不学而似。此天地鬼神能洞鉴者,后世有聪明人,必谓白石非妄语。九十一岁为橐也记。”
齐白石借助于八大脱出民间艺术的工艺性特质,蜕其躯壳,留其内核,走向文人画式的自由,得了大益处。另一方面,白石当初乃至一生喜爱八大,又突出地表明了他与一般民间艺人在趣味追求上的区别,这正是齐白石的过人处。
—郎绍君
白石老人五十岁左右的作品往往用笔很少,用色较淡而能形神兼备,气韵也生动了。这时老人的绘画艺术已经融化了八大山人的笔墨趣味,所以他对这个时期的作品特别珍视。
我藏有白石老人早期画的一张非常成功的作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秋梨上落着一只细腰蜂。秋梨已经熟透了,也许是被风摇落在地上,一只细腰蜂被梨香所吸引,刚刚飞来落在上面休息,跃跃欲动。这副小画内容十分简单,只寥寥几笔,也没有颜色,但却非常生动。画家吧大自然极平凡的一瞬间描绘出来了,所以有着丰富的生命力。
细揣摩,两笔淡墨一抹,就勾出了梨子的形象,再用较深墨加点,就画出了梨斑,墨点随水份扩散就有秋梨熟透的感觉了。然后用较干浓墨中锋一笔,画出来细而圆的梨柄,收笔时稍稍一顿,说明梨柄上端较粗而有节。梨上的细腰蜂画得更妙,只是重墨几笔勾描,就抓住了细腰蜂的形象。最生动、最难画的是两只触角,一上一下跃跃地挥动着,时时准备着要飞去的样子。
有些人自从看过这张小品后,始终不忘,可见它真有一见难忘的感染力。
六年前,我拿这画给白石老人看,他很得意,认为在笔墨上、在趣味上都与八大山人不相上下,立刻在画上题到:“此白石四十后之作。白石与雪个同肝胆,不学而似,此天地鬼神能洞鉴者。后世聪明人必谓白石非妄语。”
题后又对我解释:“四十岁以后,虽然经过多年的苦学苦练,已经掌握了笔墨技巧,但是为了获得艺术创造的条件,我随时注意对鸟兽虫鱼进行写生,体验生活,所以四十岁以后才能画出和八大山人比美的作品来,这幅是在家乡写生。我在借山馆后亲手接梨树三十余株,每到中秋,梨重约有一斤,香气四溢,味甜如蜜,每日必去树下吃梨,因而画得此稿。”这段教言我只能记得大意,从中可以了解画家一副成功的杰作是在生活中经过千锤百炼才得来的。
白石老人五十岁左右的作品往往用笔很少,用色较淡,但形神兼备,气韵十分生动。这时老人的绘画艺术已经融化吸收了八大山人的笔墨趣味,描绘自然界中的景象,自成一家。
—胡佩衡